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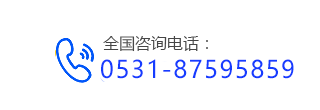
 全国免费客服电话 0531-87595859
全国免费客服电话 0531-87595859 邮箱:yiyouhengxin@163.com
手机:0531-87595859
电话:0531-87595859
地址:山东济南历下区解放路43号银座数码广场707
来源:艾尚体育APP官方网站 发布时间:2025-06-23 13:59:38 阅读:1 次

此为拙文《“肃托”与李黄之死》的姊妹篇,当初之所以没有发到本网,盖因《“肃托”与李黄之死》鲜有人问津,故没有再续贴。吊诡的是,笔者的这篇拙文,却被某人未署名转帖到他个人的网页——连文中的错误都照转不误。如果仅为蹭流量也就罢了,但还要求阅读者“订阅”就太过分了!无奈之下,笔者只好帖到本站,否则被人转帖过来就麻烦了。
本文内容最早是以《虚无缥缈的何畏枪击案》为题——作为“关山险阻渡若飞之外二篇”,于2021年9月发在笔者的公众号上。后因有关“何畏”的其它网文存在不少历史错误,故又于2023年5月重新写过并将题目改为《去伪存真话何畏》。为尊重历史,此次只对明显的历史错误予以改正,再是对错别字及“病句”等加以修正。
自改革开放以来,在众多杜撰及伪造的“历史事件”中,大概没有比原红四方面军将领何畏在长征途中枪击的“英勇事迹”更骇人听闻的了!好在当时还有不少那一历史时期的亲历者健在,所以这则虚假的枪击事件仅刊登出不到一个月,即遭到元帅的当头棒喝:“当时尚健在的元帅看了此文后十分惊讶和气愤,即令秘书致函该报,
”(注1)可叹的是“鱼死不闭目”,编造这则历史谎言的人怎肯善罢甘休?!于是,在元帅去世七年后,这则“历史谎言”经过一番改头换面之后,又堂而皇之的出现在某些媒体上。而一些心怀叵测的“好事者”及某些所谓的“网络大咖”们,为了使这则假造的“历史事件”更逼真可信,不惜通过修补原先的“漏洞”以及不合理之处,再经过一番精心的“乔装打扮”,以自媒体等形式推送给广大受众。
不言而喻,编造历史谣言有一定难处,既不能太离谱而且还得逼真,所以最终选择一个合适的主要“演员”至关重要。
根据原红四方面军老的明确回忆,其时军中的高级将领中,曾有两人对自己的属下开过枪:一个是余天云,有数次开枪的记录:如在一次行军途中,因路滑被摔落马下,拔出枪来,就将其马夫击成重伤;另外一个则是何畏,有一次开枪的记录:同样也是在一次转移途中,因遭到敌军的袭击,迁怒于作战科长周希汉。当周希汉与其据理争辩时,惹得何畏勃然大怒,拔出手枪就朝其连开五枪!
据原四方面军的老回忆,余天云不仅三次开枪造成两死一伤的难以处理的后果,而且性格强悍桀骜不驯,除张国焘等极少数领导外,就连陈昌浩都对他有点儿无可奈何!据曾任张国焘警卫排长的何福圣回忆:在某次红大的课堂上,余天云不仅当面顶撞,而且口出狂言,惹得大怒,表示不处分他绝不再上课!随即“余天云恼羞成怒,蓦地拔出手枪,对准便要开火,幸被其他学员上前拉住。 ”(注2)
至于何畏,不仅只有一次开枪的记载,而且也未造成任何人员受伤或死亡。有趣的是,文中的说法是何畏的枪法不行,也有文章的说何畏只是吓唬吓唬周希汉——那五枪射向他的身体两侧。可何畏开枪是在行军的路上,他与周希汉之间的距离不会太远,如果有意为之怎么会打不中呢?不难想象,何畏朝周希汉发火时周边肯定还会有其他人——如司令部的参谋、通讯员及警卫等,所以何畏只能是朝天开枪泄愤而已。
依据上述回忆不难判断,显然选择余天云作为枪击案的主角更为合适,更何况何畏对余天云也畏惧三分——据说一次两人发生争吵,余天云不仅要冲过去打何畏而且连枪都掏出来了,后被大伙儿抱住才算完!那么,既然余天云如此桀骜不驯又有多次开枪打自己的记载,杜撰这则谎言时为何不选他反倒是何畏呢?
说起来何畏同余天云还真是一对“冤家”,利用余天云无故顶撞的机会,时任“红大”政委的何畏得到张国焘的支持,借机狠整桀骜不驯的余天云——在部队转移时,命令余天云同其他违纪士兵一样,扛着粮袋行军。气得余天云躺在地下不肯走,被抬在担架上行进。之后听说他老婆的死讯更加想不通,在行军过大金川激流之上的悬桥时,突然翻身跳进悬崖下的激流中自杀身亡。
1937年西路军失败后,中央在3月下旬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,清算“国焘的错误问题”时,何畏的检讨只有三句话:“中央宣布国焘路线的破产,凡是革命者没有不同意的。”“我在国焘路线上,犯了军阀主义、土匪主义、反党反中央的严重错误。我只有诚恳接受这一错误。我坚决来改正我的错误,希望们帮助我。”“我对过去错误,我失去了阶级立场,我坚决来改正错误。”(注3)
从上述这三句话可以体会出,何畏的检讨显然是不得已而为之。二十天后在其警卫员的帮助下,何畏悄然离开延安,脱离了革命队伍!对于何畏其后的行踪说法不一:有说是投奔,在特务机关任中统专员;有说何畏没有去当特务,而是专门去研究中国农业并成为南京金陵大学农经系的讲师。关于何畏的离世亦有三种说法:一是1949年解放前夕被抓获遭到处决;二是渡江前夕投江自尽。还有一种说法是何畏悄悄回到广东,隐姓埋名直到1960年方辞世。
选择何畏还有个原因,主要是因为档案资料的缺失,有关何畏参加革命前后的经历有些过于简单,如此便留出遐想及杜撰的空间与可能。其后,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,如果仅是出于填补空白的考虑,产生一些不实之词尚有情可原,但有些则是另有所图。
关于何畏的经历,初始甚为简单:原名何世富,祖籍广东海南,出生于1900年农历三月十五日。童年时代随父亲何良炳来到马来亚,就读于当地的中华学校,改名为何敬贤。其后因某一些原因返回中国(具体时间不详),按照张国焘的说法“原是香港的洋服工人”,“参加过一九二五年的省港大罢工”。1927年参加“广州起义”,并于年底加入,并化名为“何畏”。1929年夏广东省委派往广西工作,参加“百色起义”,在红七军担任连长。来到中央苏区后担任独立营营长。后去上海,于1931年5月被派往红四方面军,历任团长、副师长、师长及军长等职。(以下略)
后在王建英2000年出版《中国红军人物志》中,增添了一些内容:主要有越南人,大革命时期加入,参加过工人运动,考入黄埔军校,参加北伐战争等。之后,大概是出于某种需要,有些文章在此基础上“添油加醋”——主要为:加入马共,并为中区委员;被驱逐回国后考入厦门大学,并改名为“何畏”;读书期间,与郭沫若等共同创立“创造社”;毕业后被派往香港工作;1926年3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,并于是年底加入——如此一来,何畏的入党时间,就这比原来记载提前了一年。
那么,上述这些添加的说法孰真孰假?这可借助可靠的文献资料及史料记载,通过时空及逻辑进行推敲与检验。
依据其参加1925年6月开始的省港大罢工推断,何畏应不迟于1925年初来到香港并成为制作“洋服工人”。可根据明确的文献资料记录,马来亚成立于1930年的4月30日,即使最早的南洋也是于1926年10月才在新加坡才成立!所以,不知何畏这加入马共以及担任地区领导人,从何而谈起。
经查,厦门大学的开校式于1921年4月6日举行,初创时只设有师范(包括文、理科)、商学两部(系)。由何畏进抵香港时间推断,何畏如果在厦大读过书,一定只能是前两届毕业生。但在厦大名人录中,并未发现“何畏”的大名。至于说毕业后被派往香港工作,很难令人置信!其时的大学毕业生可谓“凤毛麟角”,而且怎么能派一个党外人士去香港开展工作?!更何况直至省港大罢工结束,何畏仍然没有加入。
既然是否毕业于厦大存在疑问,那何畏在厦大读书期间参与创立“创造社”会是真的吗?“创造社”是由郭沫若、郁达夫等于1921年6月8日在日本的东京创立的——这是明确且有案可查的。该社的早期成员中的确有个名为“何畏”的,但这个“何畏”是有“创造社的眼睛”之称的著名文人何思敬的笔名。所以此“何畏”非彼“何畏”!
关于何畏于1926年3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的说法,表面上看似无问题,黄埔军校第五期入伍生中,确实有个名为“何畏”的。但中国重姓名的人很多,稍微检视便可发现两人并无相同之处:首先黄埔五期入伍生“何畏”的籍贯为湖南道县,而且其家庭住址明确记载为“道县城内玉泉坊十七号”;其次,年龄也不相符——此“何畏”入校时,年仅二十岁;再是,两人的长相也大不相同,请见下图:
这当然是不会是“无的放矢”!依据之后添加的“料”推断,之所以硬要将何畏说成是黄埔五期生,显然是为了将何畏加入的时间提前一年做铺垫。但改为1926年入党,总得有缘由或依据吧!所以,将黄埔五期的彼何畏“改头换面”为此何畏,就成为势所必然。可这需要有个前提,那就是黄埔五期的“何畏”至少应该是党员,应该具有1926年底加入的党员的经历。
依照曾庆榴撰稿的《黄埔军校前六期的员》一文记叙,第五期学生中的党员共21人,内中并无“何畏”的大名。尽管文中注明:“如下名单,仅仅是从其他有关的文章或回忆资料中找出来的,因而是很不完全的。”但这却是“因种种原因,许多教职员、学生的名字未能在第五、六期‘教职员名录’和‘同学录’登记,……”(注4)所致。可这何畏的大名,却是清清楚楚地记录在档,所以他不会是党员。
大概是心中有所怯懦——毕竟没找到任何证据,因而为了给“何畏”1926年底加入的“假说”增加有利的砝码,始作俑者便将北伐军政工人员一张合影中的某人,毫无依据地硬说成是“何畏”,企图通过此照片来证明何畏不仅是于1926年加入,而且还是在北伐军中的高级政工人员!
按照网络上流行的“有图有真相”的名言,这个“指鹿为马”的造假手段,还真起到了“以假乱真”的作用!随后,不仅等有关何畏的“词条”不问青红皂白地加以引用,不少文章更是趋之若鹜般的跟着上当受骗——例如某篇于2015年11月发表的有关北伐的文章,直截了当地在引用这张照片时标明“后排右一何畏”!
那么,照片上那个人不是何畏又会是谁呢?始作俑者为何敢明目张胆地将其说成是何畏呢?请看本文是如何剥下其“伪装”的。
不言而喻,始作俑者之所以敢如此胆大妄为,盖因这张年代久远,不仅照片拍摄的时间说法不一,而且照片上的人物说明混乱且不够完整,这就难免给别有用心的人,留下了造假的余地与可能。
根据笔者查证,这张历史照片,较早出现在《李一氓回忆录》中——该书首版于1993年,是由李一氓亲自收集资料并写成。可惜的是,修改了八章(共十章)之后,老人便一病不起!所以书中对照片中的人物,只做了简要的介绍:“北伐军占领南昌后,部分政治工作人员的合影。前排左二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,左三第三军党代表朱克靖,左四为第二军党代表李富春。”(注5)
那么,这张历史照片究竟拍摄于何时何地?这对于判定右上角那人到底是谁,为何笔者否认是“何畏”,具有决定性的意义。
根据笔者查证,这张照片摄于1926年的9月20日,即北伐军第一次攻克南昌的第二天,在北伐军中从事政治工作的员们在南昌行辕的合影。依据文献资料记录,黄埔军校第五期入伍生从1926年3月起开始入学,11月经考试升为正式学生,直至1927年8月15日方毕业。因此照片上那人,断无可能是黄埔五期生的何畏!
那么,这张照片上的人物都是谁呢?笔者经过反复搜寻比对,大概能确定的为:前排左二为郭沫若,左三为朱克靖,左四为李富春;第二排左一为杨贤江,左二为赵子俊,左三为彭年,左四为卢立群;第三排,左一为成仿吾,左二为李一氓,左三为林伯渠,左四为廖乾武,左五为方维夏,左六(即右一)为
。有的人觉得前排左一是周士第,但他其时为叶挺部团长——并非政工人员。有人认为是杨贤江,但杨是近视眼,平时戴眼镜。所以两者应该都不是,故只能暂且存疑。
那为何能确定右上角那位系罗汉而非何畏呢?除了上述所言的黄埔五期生何畏尚在黄埔军校学习——既未参加北伐战争,更不有几率会成为北伐军的高级政工人员!而罗汉不仅于1920年与周恩来、李立三、王若飞等一同赴法勤工俭学,而且还是早期党员——1922年加入。1924年8月进入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员,北伐时担任第四军副党代表。所以孰是孰非不难分辨。此外,还能够最终靠照片,进行比对:
令人遗憾的是,罗汉后来与渐行渐远——1927年底,受中央派遣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。期间,中国学生被卷入托洛茨基派与斯大林派的斗争。1928年秋,罗汉回到上海,等待分配工作。尔后,中央派往北京,进行革命活动。1930年春,与刘仁静、王文元(王凡西)等留苏学生组织了“十月社”,宣传托洛茨基的理论和观点并正式与脱离了组织关系。
1937年抗战爆发,早已脱离“托派”组织关系的陈独秀派罗汉等,与代表商谈重回事宜。但后来因王明等的阻拦,并诬蔑陈独秀为“汉奸”,致使商谈夭折。其后作为陈独秀的学生,罗汉一边照顾着陈独秀晚年的生活,一边以电木工程师的身份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少将技术员(军委会工兵署技术员)——从事技术工作。1939年5月3日上午,罗汉在日军飞机轰炸重庆时遇难。
通过以上分析考证及比对不难分辨,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所添加给何畏头上的“光环”大都为无稽之谈,只是想为编造“枪击案”增加点儿可信度罢了!
仔细阅读这桩杜撰的“历史事件”辗转起伏的过程,就能发现一个十分有趣的“奇特”过程(或曰“现象”):为了弥补早期编造中出现的“漏洞”,先是将之前所说的“毛儿盖会议”改为了“一、四方面军联席会议”,并将时间也改为了
;其后,又将何畏开枪“哒哒哒……”留下十个弹孔,聪明地改为“十余个弹孔”,进而有“大咖”干脆描述为“一梭子”!那么,经过如此这般“修补”,是否意味着这则杜撰的“枪击案”就能成立呢?
中央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,出席此次会议的有张闻天、、博古、王稼祥、陈昌浩、凯丰、邓发、、李富春、、和共十二人。朱德和张国焘因在左路军未能参加会议,而周恩来因重病也未到会。之所以召开此次会议,是为客服张国焘的分裂危险,督促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,以实现和执行两河口会议所做出决议。那么,何畏为什么没有出席此次会议?查一下史料记载就会明白,其时根据中央的决定,将整个部队分为左、右两路北上,何畏率领的二十七师等四个团组成懋功支队,留在后面掩护主力部队的北进。
查一下文献史料便可知晓,在这个时间段召开的仅有一次会议,就是由其时“党内负总责”的洛浦(张闻天)主持召开的政治局会议——既史称的“沙窝会议”。依据文献档案记载,出席此次会议的有张闻天、、周恩来、博古、朱德、张国焘、邓发、凯丰、陈昌浩、、傅钟共十一人,王稼祥因病未能到会。
上述这段史实雄辩地证明,根本不可能有什么“一、四方面军联席会议”——试问,分身乏术的、周恩来、朱德、张国焘等,如何能主持召开或出席这样一个子虚乌有的捞什子会议?“英勇无比”的何畏,又如何能看到不在场的张国焘使出的眼色,朝着根本就无法出席会议的、周恩来开枪射击呢!?还“哒哒哒……”射出十枪,“十余”枪和“一梭子”!
对那段历史知道的都明白,当时能实行连发的自动手枪,应该只有带快慢机功能的“驳壳枪”。其时军队所用的二把(号)“驳壳枪”约三十公分长,平时装在一个硕大的木头盒子里,这也就是所谓“匣子枪”的由来。
对驳壳枪知道的都明白,要想从木匣子中抽出驳壳枪来绝非易事——即使简易的皮枪套也是一样——需要左右两手配合,打开盒盖后一手按住外壳、另一只手抓住枪把才能顺利从匣子里抽出。为避免走火,置放在木壳(枪套)中的枪是不能子弹上膛的,机头(击锤)更是不能打开!否则难保不会走火。
据此可以简单地推想一下,那个杜撰的“射击事件”能否成立:即使何畏能够毫无阻拦地挎着“驳壳枪”,雄赳赳、气昂昂进入大会会场,当他准备开枪时必须要先站起来,然后将枪抽出来子弹上膛,再将开关拨到“自动”上,才能完成开枪射击!试想,要想完成这一连串的动作,即使再熟练,没有个三秒两秒的能完成吗?!
此外,当何畏手忙脚乱地开始抽枪准备射击时,坐在旁边的难道只是默默无语看着他完成这一系列动作吗?!所以除非无意阻拦,否则当何畏准备抽枪时只要用手轻轻向下一按,杜撰者精心编制的“见势不妙一把握住何畏的手臂,奋力向上举起,……”,就只能被扼杀在阴谋者的“襁褓”之中!
自古以来,但凡造假很难自圆其说!而编造“何畏枪击”事件的始作俑者,又犯了粗枝大叶不问所以的毛病——连基本的功课都未能做足。先不说作为老革命的何畏是否会有意犯下如此大错,其时他根本就不具备完成拔枪射击这一整套动作的能力!为了方便阅读与理解,请参考下面这张照片:
稍微留意便可发现,照片中的何畏,有意识地侧着身子。为啥不从正面拍照呢?道理非常之简单,何畏要避免被看到他残废的左臂。
根据相关史料记载,1933年的10月3日,红九军在攻打大庙场、新店子一线的敌军阵地时,一发炮弹落在军长何畏身旁——左半边身子被炸伤!战后经过治疗命保住了,但却失去了大半个左臂!
这里需要非常申明的是,本文贴到笔者的公众号上后,很快就有网友指出:这张照片上的人物并非何畏,而是张宗逊将军!有趣的是,那位转帖者却照单全收。
笔者注意到,“何畏枪击”的历史谎言遭到元帅义正辞严的驳斥后,曾一度销声匿迹了好一阵子,一直蛰伏到九十年代才又重新浮出水面。那为什么总有人时不时乐此不疲地利用各种机会宣扬这则假历史呢?
笔者以为,除了某些人为赚取眼球和流量之外,始作俑者显然另有所图。表面上看似乎是批张国焘与何畏,实际是要通过这则虚无缥缈的枪击案达到某种目的——试想,何畏竟然敢公开向开枪射击,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什么?至少说明其时的中央对实力强大的红四方面军无可奈何!令人可笑的是,某些人似乎乐见这则谎言的流传——好像能从中得到某种莫名的快感似的。
众所周知,所有的事情都有个发展过程。实事求是地说,会师之前,张国焘指挥的红四方面军不遗余力地配合中央红军的行动!会师后,张国焘甚至煞费苦心安排所部,尽可能为中央及中央红军提供好的物资供应。张国焘与中央的分歧是在会师后的战略选择上,在“两河口会议”上,双方矛盾才初露端倪。张国焘如果当时真有要改变政治局格局的想法,采用武力解决即可——其时四方面军有八万多雄兵、一方面军只有两万来人还是疲惫之师,安排何畏开枪枪杀中央主要领导如何向全党全军解释!?
伪造者大概忘记了这样一个最基本的事实,红四方面军同样是领导的队伍,如果张国焘等不是中央派遣过去的,红四方面军的将士们那能听从他的领导!此外,无论之前还是之后中央(包括史学界)经研究得出的结论,张国焘在长征途中确实有携裹中央及红军南下的企图,但未曾发现有企图武力解决中央的实质性行为!
正如以上分析的那样,在这则虚构的历史“段子”里,不仅是何畏拔枪射击的描写,几乎所有关键环节都经不起历史的推敲!笔者感到,那些人们之所以敢如此编造,还在于要证明“有”易、证明“无”则难上加难!人家说历史上“有”,时过境迁的今天你想要证明其“无”,绝不是件容易的事!——没有的事如何来证明呢?
幸好地球人没有“分身之术”,否则真的没办法证实——假如有人笃信天上有神仙,恐怕你就是说破天,也难以证明天上根本就没有神仙存在!
笔者感到不可思议的是,这则虚假得历史事件之所以死而不僵,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某些“好心人”的“涂脂抹粉”。例如,某位网络“大咖”栩栩如生般描述道:“气愤地下掉何畏的手枪,‘叭’的一下放在毛主席的面前。”“当大家转过神来看时,只见他还是那样巍然不动,微微笑着,在用平静的眼神巡视着们,然后若无其事地向房顶上看了看,嘴角上露出讥讽的冷笑。”(注6)
更令人匪夷所思是表面上看,这些添加的内容似乎是在颂扬的宽宏大量,实际却是有损于的尊严和大智大勇!假如何畏真的将一梭子子弹全部搂光,说明他是一定是要将对方置于死地!怎会是仅以“是何军长的枪走火了”,就定性为“这是个例外,不必再追究了。”(注7)?!纵观一生的革命经历,虽不失大度,但在原则问题上却从来不做让步!所以,还是不要自以为是为好,以免贻笑大方!
对于这种有意为之的恶劣行为,西安电科大的杨建业教授早在本世纪初,就在其撰写的文章中感慨道:“如此讹传,一般读者若未能有幸读到当年《文摘报》上徐帅办公室的这则来函,对此‘掌故’真耶假耶,又怎能辨清?
”(注8)行文至此无需赘言,谎言就是谎言,再怎么传播也变不成事实!纵观人类历史,任何欲通过造假来改变历史的企图,都会在真理面前被击得粉碎!
注2:见何福圣口述、罗学蓬撰《贴身侍卫的回忆-红黑黄白张国焘》,2001年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出版,第176页。
注4:出处——黄埔军校前六期的员 - 综合资料 - 抗日战争纪念网
新闻中心